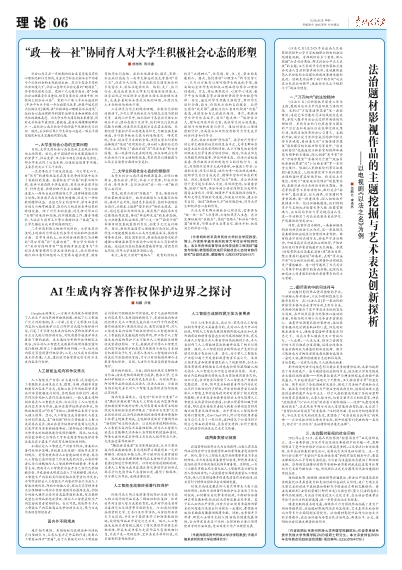发布日期:
“政—校—社”协同育人对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形塑
■ 胡彬彬 陈宇鑫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心理状况和行为倾向,是身处于社会坐标体系中的每个个体对社会的主观能动反映。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把社会心态治理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而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脊梁,同时也是社会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批判精神的群体之一,其社会心态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先行指标。因此,关注和引导大学生社会心态是一项关乎国家稳定和未来发展的现实议题。
一、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主要问题
目前,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在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趋势。然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高速跃迁的背景下,社会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被高度浓缩,部分学生出现了心态失衡、价值观念偏离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压力下的过度焦虑。对大学生而言,对“优秀”的持续性追求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成为了普遍性的焦虑。随着社会中“内卷”现象不断加剧,竞争不再局限于学业成绩,更是延伸至实习经历、科研竞赛、社团任职乃至方方面面。学生们被迫卷入一场场自我证明游戏之中,这种持续的比较与追赶,使焦虑不再是偶发的情绪,而成为一种弥散的精神状态。在这无休止的循环中,学习本身的价值与兴趣常被悬置,取而代之的是对竞争结果的持续忧虑。除了对学业的焦虑,还包括对毕业后“出路”的迷茫和恐惧,找不到理想工作、薪资待遇低、无法在大城市立足等方面的担忧。“焦虑”成为大学生描述自我日常的高频词汇。
二是价值判断上的功利化倾向。大学生在价值观上的功利化倾向表现在学习动机和职业选择方面。在学习动机上,知识的价值被转化为清晰的“得分逻辑”和“兑换功能”。部分学生倾向于以“是否对保研有利”“能否提升就业竞争力”为标准来衡量课程与学术活动的意义,然而那些短期内难以看到回报的人文素养与通识教育,则容易被学生们忽视。在职业选择方面,稳定、高薪、社会地位高成为一些学生择业时优先考虑的“金三角”,而在个人兴趣、专业匹配度与国家社会的长远需求上,则往往退居次位。编制、大厂、热门行业、发达地区成为大学生们竞相追逐的焦点,这背后既是对经济安全感和体面生活的理性追求,也夹杂着对社会潜在风险的回避,必然引发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三是社交行为上的现实回避。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大学生的社交行为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在线上世界中,他们活跃于各类社交媒体和娱乐平台;然而在线下生活中,他们却往往表现出沉默与回避,对真实社交感到不自在甚至恐惧。长期沉浸于虚拟世界而忽视真实社交,无疑会滋生孤独感,并可能导致社交能力的逐渐退化。研究发现,学业、就业等多方面的重压,使得大学生们果断选择淘汰“低效”的现实社交,转而投入虚拟社交的怀抱,从而导致了“虚拟依赖”与“现实失能”的双重困境。这一现象所凸显出的问题,不仅体现出大学生在社交行为上的割裂状态,更表现在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质量方面的双重危机。
二、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形塑路径
大学生社会心态问题的根源复杂,必须打破壁垒,整合政府、学校、社会三方资源,形成目标同向、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政—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
首先,政府应做好“压舱石”。首先,要做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政府应继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缓解“僧多粥少”的就业焦虑。其次,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推广高校毕业生过渡性社保政策,降低“毕业即失业”的生存恐惧。大力扶持基层就业项目,将“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项目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拓宽多元化成功路径。再次,推动实施国家心理健康行动计划,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制定国家标准,推动高校按要求配齐建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业人员和硬件设施。通过政府在制度层面营造有希望、有温度的大环境,引导大学生摒弃消极心态。
其次,高校应做好“领路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高校要将“心理育人”作为宗旨之一,从专注少数有心理问题学生的危机干预,转向面向全体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和心理韧性建设。首先,要从课程设计、心理中心建设、数字平台咨询服务等方面做好资源整合和配套保障。其次,通过对学生开展生涯教育,帮助学生进行兴趣、能力、价值观方面的自我探索。让学生明白“我是谁”,摆脱与他人盲目比较的“内卷”焦虑,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再次,要推动学生评价体系改革,弱化“绩点唯一”的评价方式,增加过程性评价比重,减轻学生的分数焦虑,鼓励为兴趣和热爱而学习。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守护,使高校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成长的关怀者和引导者。
再次,社会应做好“净化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面临的社交环境复杂多元,大学生群体在接受主流价值观熏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网络亚文化等负面价值的影响。因此,社会应加大力度强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生态。依法打击贩卖焦虑、散布极端言论和制造对立的网络行为。其次,鼓励媒体宣传多元成功榜样,如基层工作者、公益创业者,改变以财富、地位为唯一标准的成功观,鼓励学生关注自我成长、精神丰富和对社会的贡献。再次,建设线下交往“拉力”系统。在公共区域设计更多适合年轻人交流、休闲的空间,如创意市集、阶梯广场等,将冰冷的公共空间转变为大学生愿意主动前往、停留、相遇并产生连接的活力场所,帮助大学生掌握社交技能,积累成功经验,建立社交自信。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环境影响,引导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
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需要整合“政—校—社”三方资源,打造协同育人生态。充分发挥好政府“压舱石”、高校“领路人”和社会“净化器”的作用,形塑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作者胡彬彬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作者陈宇鑫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嬗变与形塑:转型期民族地区积极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QNXSXF2024007)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心理状况和行为倾向,是身处于社会坐标体系中的每个个体对社会的主观能动反映。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把社会心态治理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而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脊梁,同时也是社会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批判精神的群体之一,其社会心态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先行指标。因此,关注和引导大学生社会心态是一项关乎国家稳定和未来发展的现实议题。
一、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主要问题
目前,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在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趋势。然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高速跃迁的背景下,社会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被高度浓缩,部分学生出现了心态失衡、价值观念偏离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压力下的过度焦虑。对大学生而言,对“优秀”的持续性追求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成为了普遍性的焦虑。随着社会中“内卷”现象不断加剧,竞争不再局限于学业成绩,更是延伸至实习经历、科研竞赛、社团任职乃至方方面面。学生们被迫卷入一场场自我证明游戏之中,这种持续的比较与追赶,使焦虑不再是偶发的情绪,而成为一种弥散的精神状态。在这无休止的循环中,学习本身的价值与兴趣常被悬置,取而代之的是对竞争结果的持续忧虑。除了对学业的焦虑,还包括对毕业后“出路”的迷茫和恐惧,找不到理想工作、薪资待遇低、无法在大城市立足等方面的担忧。“焦虑”成为大学生描述自我日常的高频词汇。
二是价值判断上的功利化倾向。大学生在价值观上的功利化倾向表现在学习动机和职业选择方面。在学习动机上,知识的价值被转化为清晰的“得分逻辑”和“兑换功能”。部分学生倾向于以“是否对保研有利”“能否提升就业竞争力”为标准来衡量课程与学术活动的意义,然而那些短期内难以看到回报的人文素养与通识教育,则容易被学生们忽视。在职业选择方面,稳定、高薪、社会地位高成为一些学生择业时优先考虑的“金三角”,而在个人兴趣、专业匹配度与国家社会的长远需求上,则往往退居次位。编制、大厂、热门行业、发达地区成为大学生们竞相追逐的焦点,这背后既是对经济安全感和体面生活的理性追求,也夹杂着对社会潜在风险的回避,必然引发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三是社交行为上的现实回避。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大学生的社交行为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在线上世界中,他们活跃于各类社交媒体和娱乐平台;然而在线下生活中,他们却往往表现出沉默与回避,对真实社交感到不自在甚至恐惧。长期沉浸于虚拟世界而忽视真实社交,无疑会滋生孤独感,并可能导致社交能力的逐渐退化。研究发现,学业、就业等多方面的重压,使得大学生们果断选择淘汰“低效”的现实社交,转而投入虚拟社交的怀抱,从而导致了“虚拟依赖”与“现实失能”的双重困境。这一现象所凸显出的问题,不仅体现出大学生在社交行为上的割裂状态,更表现在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质量方面的双重危机。
二、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形塑路径
大学生社会心态问题的根源复杂,必须打破壁垒,整合政府、学校、社会三方资源,形成目标同向、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政—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
首先,政府应做好“压舱石”。首先,要做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政府应继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缓解“僧多粥少”的就业焦虑。其次,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推广高校毕业生过渡性社保政策,降低“毕业即失业”的生存恐惧。大力扶持基层就业项目,将“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项目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拓宽多元化成功路径。再次,推动实施国家心理健康行动计划,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制定国家标准,推动高校按要求配齐建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业人员和硬件设施。通过政府在制度层面营造有希望、有温度的大环境,引导大学生摒弃消极心态。
其次,高校应做好“领路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高校要将“心理育人”作为宗旨之一,从专注少数有心理问题学生的危机干预,转向面向全体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和心理韧性建设。首先,要从课程设计、心理中心建设、数字平台咨询服务等方面做好资源整合和配套保障。其次,通过对学生开展生涯教育,帮助学生进行兴趣、能力、价值观方面的自我探索。让学生明白“我是谁”,摆脱与他人盲目比较的“内卷”焦虑,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再次,要推动学生评价体系改革,弱化“绩点唯一”的评价方式,增加过程性评价比重,减轻学生的分数焦虑,鼓励为兴趣和热爱而学习。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守护,使高校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成长的关怀者和引导者。
再次,社会应做好“净化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面临的社交环境复杂多元,大学生群体在接受主流价值观熏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网络亚文化等负面价值的影响。因此,社会应加大力度强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生态。依法打击贩卖焦虑、散布极端言论和制造对立的网络行为。其次,鼓励媒体宣传多元成功榜样,如基层工作者、公益创业者,改变以财富、地位为唯一标准的成功观,鼓励学生关注自我成长、精神丰富和对社会的贡献。再次,建设线下交往“拉力”系统。在公共区域设计更多适合年轻人交流、休闲的空间,如创意市集、阶梯广场等,将冰冷的公共空间转变为大学生愿意主动前往、停留、相遇并产生连接的活力场所,帮助大学生掌握社交技能,积累成功经验,建立社交自信。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环境影响,引导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
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需要整合“政—校—社”三方资源,打造协同育人生态。充分发挥好政府“压舱石”、高校“领路人”和社会“净化器”的作用,形塑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作者胡彬彬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作者陈宇鑫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嬗变与形塑:转型期民族地区积极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QNXSXF202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