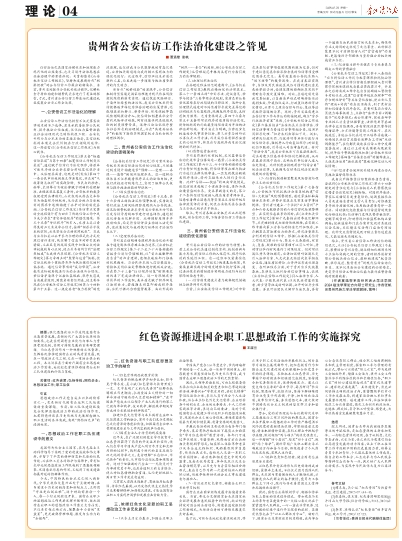发布日期:
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之管见
■ 夏遇霏 张帆
信访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为贯彻落实《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对公安信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当前,贵州省对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于此,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也亟需契合公安工作全过程。
一、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理解
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转型不仅是落实法律制度的不二选择,更是承载着保障公民权利、提升执法公信权威、优化权力监督效能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工程。公安机关作为与公民互为的直接互动者,其信访机制的本质是公民诉权在行政领域的延伸。这一转型需以《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为核心载体。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五条“畅通信访渠道”与第十四条“拓宽信访工作制度化渠道”,通过赋予信访行为法定程序,将原本可能失序的公众诉求整合到规范化程序当中。从法理层面看,这既是对《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申诉权的教义学具象化,亦是对“无救济则无权利”的实践诠释。当民众的控告、检举、求助等行为被法律赋予明确的受理标准、办理流程及答复义务时,公安机关的裁量权便受到法律制约,公众权利从静态文本转变为动态程序性权利,从而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中逐渐构建了公平对话的制度基础。《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章以完整的全流程设计有力回应了传统信访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惯性困境。第五十五条“听证程序”的引入,本质上是以看得见的正义来筑牢公信力,诠释“程序并非技术的空转,而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机制”。当我省公安机关以公开参与合理的程式化方式处理信访诉求时,既消解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猜疑,又在反复的规则实践中加强公众对法律权威的内心认同,这正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权威”生成的内在逻辑。《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七章确立的“监督与追责”机制,使信访从被动个案救济升华为执法规范化的纠偏系统。通过信访事项的“反向审视”,公安机关应检视其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若信访矛盾源于证据收集瑕疵、程序失范或自由裁量滥用,则需启动责任倒查,这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的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五条。这一规定具有“权力制衡”的宪政原理,让信访成为公民监督权的常态化渠道,公安机关则通过自我纠错以实现权力的理性化运行。此过程中,信访不仅是矛盾化解的工具,而且更进一步演进为执法质量提升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公安信访机制转型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风险控制维度的制度实现。通过执法风险评估、矛盾纠纷排查的法治化,我省公安机关将信访数据逐步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决策资源,还能够在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维权等高风险领域提前介入,使信访机制兼具社会矛盾的风险评估功能,同时还能体现系统性风险的制度预警价值。这种以法治化程序整合社会诉求的治理模式,亦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框架下渐趋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的理性调和。
二、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的逻辑架构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作为贵州省公安机关实施信访法治化的核心规范,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构建逐步“预防——受理——办理——监督”的闭环治理体系。这一逻辑治理体系不仅承载着程序正义的法治内核,更在行政权运行的维度上,实现了保障公民权利与提升执法效能的辩证统一。
(一)源头预防法治化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确立的执法风险预警机制,实质就是将行政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纳入公安执法。该风险预警机制要求贵州省公安机关对可能引发信访矛盾的环节进行动态评估,通过制度化排查而化解矛盾。此种预防原则并非被动响应,而是将信访评估主动纳入法定程序,使政策制定与权利执行始终处于法治约束之下。
(二)受理程序法治化
贵州省应该明确受理程序法治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刚性程序确立权力边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二十二至二十六条构建的首接责任制与管辖规则,以“首次接触即终身负责”的归责逻辑,能彻底破除部门推诿的制度痼疾。当公民诉求进入信访渠道时,首接机关须依法定管辖权进行甄别及分流,并在第二十三条“15日程序回复”时限要求的约束下完成法律确认。这一时限规定并非简单的工作流程,其本质是赋予程序回复以法律效力,若超期未回复即构成程序违法,公民可据此启动监督救济。由此形成的“时限——责任”的闭环,使《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从管理规范升格为具有行为指引效力的法律规则。
(三)办理过程法治化
在办理过程法治化的建构中,《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展现出精细化的法律技术。第二十一条确立的“申诉求决、建议意见、检举与控告”三类事项分流规则,实质是诉讼类型化思维在行政领域的迁移运用。这种分类治理模式通过对不同性质诉求设定差异化的证明标准与处置路径,既避免程序空转,又防范权力滥用。尤为重要的是,第四十七条与第五十五条将听证程序的适用情形法定化,使传统封闭的行政裁量过程转变为开放的法律论辩场域。贵州省应当明确,当涉及重大权益处分或事实争议时,第三方参与的听证不再仅是工作方法,而是成为具有程序法意义的必经环节,彰显出行政程序向司法化演进的时代特征。
(四)监督追责法治化
贵州省将推行双重机制,采用监督追责法治化筑牢责任落实这一愿景。《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六十三、六十四条构建的过错行为责任倒查机制,将信访事项办理与执法行为进行法律关联审查,一旦发现执法瑕疵或程序违法,将对直接承办人进行责任追溯。此种“信访——执法”的双向审视模式,使信访制度超越了个案救济功能,进阶为执法质量监测体系。更具革新意义的是,第六十二条将信访绩效纳入执法质量考评体系,这意味着群众满意度等实质正义指标开始与法律效果评价并重,促使公安机关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综上,贵州省各级公安机关正以此逻辑架构,结合实际工作,不断夯实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
三、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转型,本质上是公安机关通过制度重构、机制创新与能力再造,将信访工作纳入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的系统性工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依托《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构建基础框架,更需要直面实践中的制度缝隙与执行惰性,通过法治技术的精细设计实现权力运行与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
(一)信访制度建设应着力破解规范模糊性与救济碎片化难题
当前,《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对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受理范围的较为完善,但对于建议意见类和检举控告类的信访事项受理范围并无定义。易导致基层公安机关陷入“该不该管”的裁量困境。在我省基层实践中,当涉及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建议意见或检举控告时,受理范围的模糊性在实践中有时会导致处置困难。对此,应通过制定实施完善细则,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排除司法裁判生效、仲裁协议成立、行政复议终结等法定情形,从源头上厘清信访与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的边界。同时,贵州省亟需建立公安信访工作与诉讼的衔接规则,确立“穷尽行政救济前置”原则。《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六条虽指出“公安机关应当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与普通信访事项相分离,适用不同程序处理。”但并未列出详细下文。例如,对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访诉求,强制导入行政复议程序;对经复议仍不服的,引导进入司法审查轨道。针对“诉访分离”,我省公安机关可与各层级法院、司法局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化解机制,从而在基层实践中高效、正确地引导信访人进入法定渠道。此种制度安排既符合“诉访分离”的法治逻辑,又能避免信访渠道对法定救济制度的功能僭越。
(二)信访机制创新需聚焦风险防控与程序正义的双重目标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七条指出,公安机关可依托执法办案系统构建“信访+大数据”风险预警模型,通过算法抓取高频诉求类型、涉警矛盾焦点及重复访等事因规律。贵州省可建立一个依托“云上贵州”平台和公安大数据资源的公安信访风险预警模型。在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在《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十九条指出的争议化解环节,应突破封闭式办案的传统桎梏,在实践工作中落实第三方参与的标准化听证程序,不应搁置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将司法资源充分利用到信访工作中。根据《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十七、第五十五条授权,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引入听证,并对听证举行时间进行了时限规定。但对听证团队并无详细规定,应详细说明听证团队是引入法律专家、人大代表及社区代表等组成合议庭,通过质证辩论、公开评议形成处理意见。在听证程序方面,对于贵州为多民族聚集地,在涉及土地纠纷的信访事项上,依照《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引入法律专家、人大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民族村寨的寨老、新乡贤等组成的听证团,公开听证并全程录像。并且听证团队应倾听当地民意,并有一个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代表参加,确保程序正义的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尊重。此种程序装置不仅可消解信访人对“官官相护”的质疑,更能借助外部理性力量补强公安机关的裁量正当性。
(三)信访能力提升关键在于专业素养与群众工作的紧密融合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八条指出“应当将信访工作列为教育课程和院校必修课程”,贵州省应将信访相关课程纳入贵州警察学院相关课程或者基层实践实习中。并且在之后的实践工作中也应当鼓励纳入警衔晋升考核体系,设置“信访案件规范办理率”“程序合规性评价”等具体量化指标,使公安人员将“理论+实践”动态运用起来,利于更新法律知识储备与程序意识。在贵州基层公安人员能力培养机制上,应推行“法律专家+调解能手”双培养模式:由公职律师、院校老师等专业性人才负责证据审查、法律适用等基础法律专业训练课程,再由资深社区民警传授情绪疏导、方言沟通等实践工作技巧。在民族地区,当地公安机关还可以培养并选拔一些精通民族语言且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双语调解能手”,在化解民族地区信访工作中发挥显著成效。通过以上的角色模拟与跟班实训,使年轻干警既能精准把握《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条“首接责任制”的操作要点,又能灵活运用“换位思考”策略化解信访人对抗情绪。
(四)信访责任闭环的关键是构建公安人员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我省应严格落实信访案件终身负责制,尝试将《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责任追究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相衔接。对因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引发重复访的,追溯直接承办人员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对推诿塞责导致矛盾激化的,适用执法质量考评一票否决。同时强化纪检监察与信访监督的线索双向移送机制:信访部门发现民警涉嫌渎职、受贿等线索时,即时移送纪检监察机构立案调查;纪检监察部门在办案中发现的系统性信访风险,应反馈至信访部门启动专项治理。此种交叉监督模式既可防止责任追究虚化,又能从源头压缩权力。
综上,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路径优化,应以《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为基石,紧密结合贵州省情,通过精细化规则来缩小立法与实践之间的空隙,借助程序创新重塑公安机关的公信力,最终构建起“权责清晰、程序规范、监督有力”的现代信访法治化体系。这不仅是法治公安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贵州信访工作法治化能力提升在警务领域的深刻映射。
(作者夏遇霏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2024级法学理论方向硕士研究生;作者张帆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信访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为贯彻落实《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对公安信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当前,贵州省对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于此,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也亟需契合公安工作全过程。
一、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理解
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转型不仅是落实法律制度的不二选择,更是承载着保障公民权利、提升执法公信权威、优化权力监督效能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工程。公安机关作为与公民互为的直接互动者,其信访机制的本质是公民诉权在行政领域的延伸。这一转型需以《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为核心载体。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五条“畅通信访渠道”与第十四条“拓宽信访工作制度化渠道”,通过赋予信访行为法定程序,将原本可能失序的公众诉求整合到规范化程序当中。从法理层面看,这既是对《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申诉权的教义学具象化,亦是对“无救济则无权利”的实践诠释。当民众的控告、检举、求助等行为被法律赋予明确的受理标准、办理流程及答复义务时,公安机关的裁量权便受到法律制约,公众权利从静态文本转变为动态程序性权利,从而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中逐渐构建了公平对话的制度基础。《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章以完整的全流程设计有力回应了传统信访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惯性困境。第五十五条“听证程序”的引入,本质上是以看得见的正义来筑牢公信力,诠释“程序并非技术的空转,而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机制”。当我省公安机关以公开参与合理的程式化方式处理信访诉求时,既消解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猜疑,又在反复的规则实践中加强公众对法律权威的内心认同,这正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权威”生成的内在逻辑。《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七章确立的“监督与追责”机制,使信访从被动个案救济升华为执法规范化的纠偏系统。通过信访事项的“反向审视”,公安机关应检视其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若信访矛盾源于证据收集瑕疵、程序失范或自由裁量滥用,则需启动责任倒查,这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的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五条。这一规定具有“权力制衡”的宪政原理,让信访成为公民监督权的常态化渠道,公安机关则通过自我纠错以实现权力的理性化运行。此过程中,信访不仅是矛盾化解的工具,而且更进一步演进为执法质量提升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公安信访机制转型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风险控制维度的制度实现。通过执法风险评估、矛盾纠纷排查的法治化,我省公安机关将信访数据逐步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决策资源,还能够在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维权等高风险领域提前介入,使信访机制兼具社会矛盾的风险评估功能,同时还能体现系统性风险的制度预警价值。这种以法治化程序整合社会诉求的治理模式,亦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框架下渐趋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的理性调和。
二、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的逻辑架构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作为贵州省公安机关实施信访法治化的核心规范,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构建逐步“预防——受理——办理——监督”的闭环治理体系。这一逻辑治理体系不仅承载着程序正义的法治内核,更在行政权运行的维度上,实现了保障公民权利与提升执法效能的辩证统一。
(一)源头预防法治化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确立的执法风险预警机制,实质就是将行政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纳入公安执法。该风险预警机制要求贵州省公安机关对可能引发信访矛盾的环节进行动态评估,通过制度化排查而化解矛盾。此种预防原则并非被动响应,而是将信访评估主动纳入法定程序,使政策制定与权利执行始终处于法治约束之下。
(二)受理程序法治化
贵州省应该明确受理程序法治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刚性程序确立权力边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二十二至二十六条构建的首接责任制与管辖规则,以“首次接触即终身负责”的归责逻辑,能彻底破除部门推诿的制度痼疾。当公民诉求进入信访渠道时,首接机关须依法定管辖权进行甄别及分流,并在第二十三条“15日程序回复”时限要求的约束下完成法律确认。这一时限规定并非简单的工作流程,其本质是赋予程序回复以法律效力,若超期未回复即构成程序违法,公民可据此启动监督救济。由此形成的“时限——责任”的闭环,使《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从管理规范升格为具有行为指引效力的法律规则。
(三)办理过程法治化
在办理过程法治化的建构中,《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展现出精细化的法律技术。第二十一条确立的“申诉求决、建议意见、检举与控告”三类事项分流规则,实质是诉讼类型化思维在行政领域的迁移运用。这种分类治理模式通过对不同性质诉求设定差异化的证明标准与处置路径,既避免程序空转,又防范权力滥用。尤为重要的是,第四十七条与第五十五条将听证程序的适用情形法定化,使传统封闭的行政裁量过程转变为开放的法律论辩场域。贵州省应当明确,当涉及重大权益处分或事实争议时,第三方参与的听证不再仅是工作方法,而是成为具有程序法意义的必经环节,彰显出行政程序向司法化演进的时代特征。
(四)监督追责法治化
贵州省将推行双重机制,采用监督追责法治化筑牢责任落实这一愿景。《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六十三、六十四条构建的过错行为责任倒查机制,将信访事项办理与执法行为进行法律关联审查,一旦发现执法瑕疵或程序违法,将对直接承办人进行责任追溯。此种“信访——执法”的双向审视模式,使信访制度超越了个案救济功能,进阶为执法质量监测体系。更具革新意义的是,第六十二条将信访绩效纳入执法质量考评体系,这意味着群众满意度等实质正义指标开始与法律效果评价并重,促使公安机关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综上,贵州省各级公安机关正以此逻辑架构,结合实际工作,不断夯实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
三、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转型,本质上是公安机关通过制度重构、机制创新与能力再造,将信访工作纳入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的系统性工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依托《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构建基础框架,更需要直面实践中的制度缝隙与执行惰性,通过法治技术的精细设计实现权力运行与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
(一)信访制度建设应着力破解规范模糊性与救济碎片化难题
当前,《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对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受理范围的较为完善,但对于建议意见类和检举控告类的信访事项受理范围并无定义。易导致基层公安机关陷入“该不该管”的裁量困境。在我省基层实践中,当涉及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建议意见或检举控告时,受理范围的模糊性在实践中有时会导致处置困难。对此,应通过制定实施完善细则,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排除司法裁判生效、仲裁协议成立、行政复议终结等法定情形,从源头上厘清信访与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的边界。同时,贵州省亟需建立公安信访工作与诉讼的衔接规则,确立“穷尽行政救济前置”原则。《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六条虽指出“公安机关应当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与普通信访事项相分离,适用不同程序处理。”但并未列出详细下文。例如,对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访诉求,强制导入行政复议程序;对经复议仍不服的,引导进入司法审查轨道。针对“诉访分离”,我省公安机关可与各层级法院、司法局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化解机制,从而在基层实践中高效、正确地引导信访人进入法定渠道。此种制度安排既符合“诉访分离”的法治逻辑,又能避免信访渠道对法定救济制度的功能僭越。
(二)信访机制创新需聚焦风险防控与程序正义的双重目标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七条指出,公安机关可依托执法办案系统构建“信访+大数据”风险预警模型,通过算法抓取高频诉求类型、涉警矛盾焦点及重复访等事因规律。贵州省可建立一个依托“云上贵州”平台和公安大数据资源的公安信访风险预警模型。在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在《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十九条指出的争议化解环节,应突破封闭式办案的传统桎梏,在实践工作中落实第三方参与的标准化听证程序,不应搁置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将司法资源充分利用到信访工作中。根据《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十七、第五十五条授权,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引入听证,并对听证举行时间进行了时限规定。但对听证团队并无详细规定,应详细说明听证团队是引入法律专家、人大代表及社区代表等组成合议庭,通过质证辩论、公开评议形成处理意见。在听证程序方面,对于贵州为多民族聚集地,在涉及土地纠纷的信访事项上,依照《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引入法律专家、人大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民族村寨的寨老、新乡贤等组成的听证团,公开听证并全程录像。并且听证团队应倾听当地民意,并有一个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代表参加,确保程序正义的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尊重。此种程序装置不仅可消解信访人对“官官相护”的质疑,更能借助外部理性力量补强公安机关的裁量正当性。
(三)信访能力提升关键在于专业素养与群众工作的紧密融合
《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八条指出“应当将信访工作列为教育课程和院校必修课程”,贵州省应将信访相关课程纳入贵州警察学院相关课程或者基层实践实习中。并且在之后的实践工作中也应当鼓励纳入警衔晋升考核体系,设置“信访案件规范办理率”“程序合规性评价”等具体量化指标,使公安人员将“理论+实践”动态运用起来,利于更新法律知识储备与程序意识。在贵州基层公安人员能力培养机制上,应推行“法律专家+调解能手”双培养模式:由公职律师、院校老师等专业性人才负责证据审查、法律适用等基础法律专业训练课程,再由资深社区民警传授情绪疏导、方言沟通等实践工作技巧。在民族地区,当地公安机关还可以培养并选拔一些精通民族语言且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双语调解能手”,在化解民族地区信访工作中发挥显著成效。通过以上的角色模拟与跟班实训,使年轻干警既能精准把握《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四条“首接责任制”的操作要点,又能灵活运用“换位思考”策略化解信访人对抗情绪。
(四)信访责任闭环的关键是构建公安人员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我省应严格落实信访案件终身负责制,尝试将《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责任追究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相衔接。对因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引发重复访的,追溯直接承办人员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对推诿塞责导致矛盾激化的,适用执法质量考评一票否决。同时强化纪检监察与信访监督的线索双向移送机制:信访部门发现民警涉嫌渎职、受贿等线索时,即时移送纪检监察机构立案调查;纪检监察部门在办案中发现的系统性信访风险,应反馈至信访部门启动专项治理。此种交叉监督模式既可防止责任追究虚化,又能从源头压缩权力。
综上,贵州省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路径优化,应以《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为基石,紧密结合贵州省情,通过精细化规则来缩小立法与实践之间的空隙,借助程序创新重塑公安机关的公信力,最终构建起“权责清晰、程序规范、监督有力”的现代信访法治化体系。这不仅是法治公安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贵州信访工作法治化能力提升在警务领域的深刻映射。
(作者夏遇霏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2024级法学理论方向硕士研究生;作者张帆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