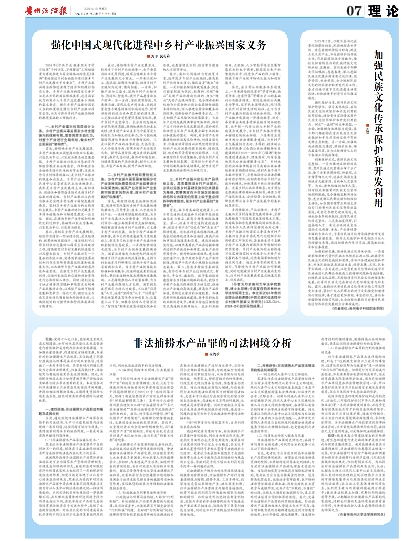发布日期: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司法困境分析
■程韵致
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越发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对生态环境以及生态资源进行有效保护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为加强水资源保护,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当前针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不仅构建了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行的双重机制,还实施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尽管针对此问题已有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规定与措施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因此,当前探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平衡严厉惩治此类犯罪与防止罪名滥用的关系。本文旨在剖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修复受损的水域生态系统,强化对该类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果。
一、理性检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适用难题及成因分析
当前,通过检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实践中的司法适用,从中可以窥见该罪司法实践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划分为两类,一类因该罪刑罚体系的缺陷所致,一类是司法实践中操作问题所致。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法益认定不一
笔者认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中出现判决不一的现象,根源在于各地法院对该罪名所旨在保护的法益存在认定上的差异。
我国现阶段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保护法益的认定可分为国家水产资源的管理制度、水域生态环境两种形式,虽然刑法对环境犯罪科处刑罚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环境法益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以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的观点,笔者认为实践中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存在的类案不同判现象正是因为对以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缺乏统一标准所造成的。不同司法机关对法益论这一学说理解不同,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所适用的手段与刑罚也相应不同,这就导致水产品的生态价值没有显性地存在于司法决断中,忽视了生态的价值规律。对法益认定的不同造成司法机关量刑不同以及对于生态修复重视程度的不同,同时也造成实践中的司法难题。
(二)法律适用标准不明确,打击威慑力不够
由于现行刑法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规定具有模糊性,为此,《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12号)通过列举方式,明确了构成该罪情节严重的五种具体情形(详见该解释第三条)。其中对于之前学者所提出建议加入的“非法捕捞为业”“多次非法捕捞的”“在非法捕捞过程中抗拒执法”也作出回应。然而,对于第五种情形,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该解释仍保持模糊表述,未提供具体细致的定罪准则。实践中,大量案件并不吻合前四种明确情形,而“其他情节严重”的模糊性,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时易产生认知分歧,进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量刑缺乏具体标准,也会造成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的问题。即使按照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但法院在量刑上也会考虑多重因素,例如犯罪人实际捕捞量小,系初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法院所作出的量刑较轻,并且对犯罪人实行较多非监禁刑。因此尽管每年查处大量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此类犯罪行为仍然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未能发挥自身的威慑作用和教育作用,实际取得的效果与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相差较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又称为“行刑衔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典型的行政犯罪,在司法实务中,此类犯罪不可避免会涉及“行刑衔接”问题。良好的“行刑衔接”机制,能够使得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过程中,当行为符合全部犯罪构成要件,行政违法行为能顺利转化为刑事犯罪行为,从而实现行刑处罚的对接。但事实上,即使有相应的协作条例,行政区划之间仍然各自为政,信息壁垒仍然存在。因此为避免自身陷入困境,行政机关将打击环保违法犯罪的压力转嫁给司法机关,大量本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消化的案子移送至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又不得拒绝裁判,从而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同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也存在协作机制缺位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四)刑事责任处罚配置不当,自身刑罚体系存在缺陷
通过研究有关案例可知,非法捕捞水产犯罪案件量刑较轻,判处自由刑比例不高,即使判处自由刑后也大多适用缓刑,该罪在对于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上十分随意,并且过多滥用从宽量刑情节导致从宽情节功能的扩大化适用。笔者认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上对于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观念尚不完善,导致刑罚力度不够以及刑罚处罚手段单一等问题的出现。
非法捕捞水产的行为对水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具有滞后性,非法捕捞水产的行为随着捕捞能力增强,捕捞手段、工具多样化,犯罪造成危害后果渐趋严重,破坏程度加剧,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幅度普遍偏低,极有可能出现刑罚与所造成的损害不相匹配的情形。此时法定刑仍坚持原有量刑标准,显然与当前的非法捕捞现状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相适应,这既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实现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效能。
二、完善路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法律适用的相关机制探索
(一)树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
笔者认为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处理中应当树立并贯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基本涵盖了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观的基本合理内核,如注重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同时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不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保障人类需求的同时十分重视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笔者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法初衷相统一,法律肯定只有将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利益糅合的法律才能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纳,也更能起到打击犯罪的作用。
(二)刑罚体系的深入探索与完善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良好运行,依赖于对刑罚体系的完善,对刑罚体系的完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首先,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提高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标准。该罪法定刑标准的设置相对较低,如果继续适用原法定刑标准,与当前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处理态度背道而驰。为达到切实有力的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提高量刑标准。适度提高犯罪成本,让违法者有所敬畏,在严格的法律责任面前不敢犯法,同时也对民众具有教育与威慑作用,让其产生“不敢犯,不想犯”的心理,从根本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真正实现刑法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其次,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罚辅助措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被告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适当增加教育性刑罚辅助措施能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如公开悔过、赔礼道歉等。通过增加教育性刑罚辅助措施,能够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使其认识到非法捕捞行为的危害性。
(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
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此类问题的处理,形成了“达到规定标准以上就是刑事案件,没有达到标准即为行政案件”这一绝对的“出行入刑”的观念。但判定行为是否构成行政犯罪,不光要其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还应该考虑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因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设置在社会管理秩序这一章,所以其保护法益不应当只包括国家水域生态资源制度,还应当体现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
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渐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出台,正逐步完善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刑法不应当过度扩张,造成行刑错位。而应当在行政处罚能解决的范围内,承担兜底作用。当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达到刑事标准边界时,应当首先选择适用行政处罚,在标准之上才适用刑法,以此保证刑法的谦抑性。
结语: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推进,对生态环境进行更全面的保护是顺应时代与现实发展的需求。面对我国渔业资源日益遭到破坏,非法捕捞行为屡禁不止的这一乱象,对非法捕捞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调整并加强对非法捕捞行为刻不容缓。《刑法》虽然做出相应规定,但仍有明显不足。为此提出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现实应对,包括:从理念上确立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将人类对环境合理的主观伦理需求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该类犯罪的所追求的司法效果;在立法上完善该罪的刑罚体系,从刑罚手段与刑罚辅助措施两方面着手;最后再从制度上加强、完善行刑衔接机制等手段,以期解决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现实困境,同时也对其他生态环境类犯罪有启示作用,为更好地保护人类生态资源环境尽些绵薄之力。
(作者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越发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对生态环境以及生态资源进行有效保护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为加强水资源保护,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当前针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不仅构建了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行的双重机制,还实施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尽管针对此问题已有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规定与措施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因此,当前探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平衡严厉惩治此类犯罪与防止罪名滥用的关系。本文旨在剖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修复受损的水域生态系统,强化对该类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果。
一、理性检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适用难题及成因分析
当前,通过检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实践中的司法适用,从中可以窥见该罪司法实践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划分为两类,一类因该罪刑罚体系的缺陷所致,一类是司法实践中操作问题所致。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法益认定不一
笔者认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中出现判决不一的现象,根源在于各地法院对该罪名所旨在保护的法益存在认定上的差异。
我国现阶段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保护法益的认定可分为国家水产资源的管理制度、水域生态环境两种形式,虽然刑法对环境犯罪科处刑罚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环境法益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以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的观点,笔者认为实践中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存在的类案不同判现象正是因为对以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缺乏统一标准所造成的。不同司法机关对法益论这一学说理解不同,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所适用的手段与刑罚也相应不同,这就导致水产品的生态价值没有显性地存在于司法决断中,忽视了生态的价值规律。对法益认定的不同造成司法机关量刑不同以及对于生态修复重视程度的不同,同时也造成实践中的司法难题。
(二)法律适用标准不明确,打击威慑力不够
由于现行刑法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规定具有模糊性,为此,《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12号)通过列举方式,明确了构成该罪情节严重的五种具体情形(详见该解释第三条)。其中对于之前学者所提出建议加入的“非法捕捞为业”“多次非法捕捞的”“在非法捕捞过程中抗拒执法”也作出回应。然而,对于第五种情形,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该解释仍保持模糊表述,未提供具体细致的定罪准则。实践中,大量案件并不吻合前四种明确情形,而“其他情节严重”的模糊性,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时易产生认知分歧,进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量刑缺乏具体标准,也会造成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的问题。即使按照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但法院在量刑上也会考虑多重因素,例如犯罪人实际捕捞量小,系初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法院所作出的量刑较轻,并且对犯罪人实行较多非监禁刑。因此尽管每年查处大量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此类犯罪行为仍然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未能发挥自身的威慑作用和教育作用,实际取得的效果与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相差较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又称为“行刑衔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典型的行政犯罪,在司法实务中,此类犯罪不可避免会涉及“行刑衔接”问题。良好的“行刑衔接”机制,能够使得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过程中,当行为符合全部犯罪构成要件,行政违法行为能顺利转化为刑事犯罪行为,从而实现行刑处罚的对接。但事实上,即使有相应的协作条例,行政区划之间仍然各自为政,信息壁垒仍然存在。因此为避免自身陷入困境,行政机关将打击环保违法犯罪的压力转嫁给司法机关,大量本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消化的案子移送至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又不得拒绝裁判,从而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同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也存在协作机制缺位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四)刑事责任处罚配置不当,自身刑罚体系存在缺陷
通过研究有关案例可知,非法捕捞水产犯罪案件量刑较轻,判处自由刑比例不高,即使判处自由刑后也大多适用缓刑,该罪在对于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上十分随意,并且过多滥用从宽量刑情节导致从宽情节功能的扩大化适用。笔者认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上对于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观念尚不完善,导致刑罚力度不够以及刑罚处罚手段单一等问题的出现。
非法捕捞水产的行为对水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具有滞后性,非法捕捞水产的行为随着捕捞能力增强,捕捞手段、工具多样化,犯罪造成危害后果渐趋严重,破坏程度加剧,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幅度普遍偏低,极有可能出现刑罚与所造成的损害不相匹配的情形。此时法定刑仍坚持原有量刑标准,显然与当前的非法捕捞现状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相适应,这既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实现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效能。
二、完善路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法律适用的相关机制探索
(一)树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
笔者认为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处理中应当树立并贯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基本涵盖了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观的基本合理内核,如注重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同时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不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保障人类需求的同时十分重视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笔者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法初衷相统一,法律肯定只有将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利益糅合的法律才能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纳,也更能起到打击犯罪的作用。
(二)刑罚体系的深入探索与完善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良好运行,依赖于对刑罚体系的完善,对刑罚体系的完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首先,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提高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标准。该罪法定刑标准的设置相对较低,如果继续适用原法定刑标准,与当前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处理态度背道而驰。为达到切实有力的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提高量刑标准。适度提高犯罪成本,让违法者有所敬畏,在严格的法律责任面前不敢犯法,同时也对民众具有教育与威慑作用,让其产生“不敢犯,不想犯”的心理,从根本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真正实现刑法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其次,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罚辅助措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被告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适当增加教育性刑罚辅助措施能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如公开悔过、赔礼道歉等。通过增加教育性刑罚辅助措施,能够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使其认识到非法捕捞行为的危害性。
(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
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此类问题的处理,形成了“达到规定标准以上就是刑事案件,没有达到标准即为行政案件”这一绝对的“出行入刑”的观念。但判定行为是否构成行政犯罪,不光要其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还应该考虑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因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设置在社会管理秩序这一章,所以其保护法益不应当只包括国家水域生态资源制度,还应当体现对于生态法益的保护。
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渐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出台,正逐步完善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刑法不应当过度扩张,造成行刑错位。而应当在行政处罚能解决的范围内,承担兜底作用。当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达到刑事标准边界时,应当首先选择适用行政处罚,在标准之上才适用刑法,以此保证刑法的谦抑性。
结语: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推进,对生态环境进行更全面的保护是顺应时代与现实发展的需求。面对我国渔业资源日益遭到破坏,非法捕捞行为屡禁不止的这一乱象,对非法捕捞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调整并加强对非法捕捞行为刻不容缓。《刑法》虽然做出相应规定,但仍有明显不足。为此提出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现实应对,包括:从理念上确立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将人类对环境合理的主观伦理需求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该类犯罪的所追求的司法效果;在立法上完善该罪的刑罚体系,从刑罚手段与刑罚辅助措施两方面着手;最后再从制度上加强、完善行刑衔接机制等手段,以期解决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现实困境,同时也对其他生态环境类犯罪有启示作用,为更好地保护人类生态资源环境尽些绵薄之力。
(作者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