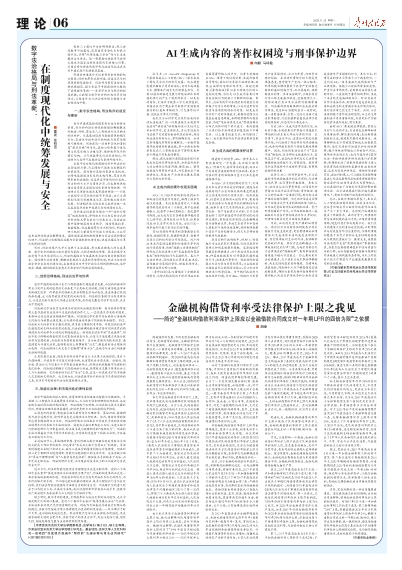发布日期:
数字法治格局与刑法革新:在制度现代化中统筹发展与安全
■曹波 张钧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并将“统筹发展与安全”作为未来发展的总体要求。这一部署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而国家安全理念的数字化与法治化也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科技的快速进步不仅重塑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同时也带来风险形态、法益边界与制度逻辑的深层转变。刑法作为国家法治体系的底线规范,理应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大格局下实现理性革新——既坚守安全与秩序的制度底线,又能够与数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相适应,以制度定力与法治理性维系创新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一、数字安全格局:刑法秩序的适应与更新
数字中国建设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的整体重塑,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物理防御拓展至对数据、网络、算法及人工智能运行体系的系统性维护。信息基础设施与数据资源的稳定安全,直接关乎社会运行的韧性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性。刑法在这一结构中仍承担着制度“最后防线”的角色,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确立规范底线与法益边界,维护数字秩序的稳定结构。与行政监管或行业标准相比,刑法的介入始终代表着法治体系的终极约束。
在数字安全格局的演进过程中刑法并非主动治理力量,而是随时代演进自我调适的制度规范。面对新兴风险的复杂生成机制,如跨境数据流动引发的主权问题、算法失衡带来的社会操控、信息泄露导致的信任危机,刑法的回应不应当盲目扩张,而需要理性地通过适度修正实现法治体系的内部协调。刑法的应变逻辑体现在其审慎的特性——它既不能固守旧有结构而脱节于现实,亦不应因短期风险而突破制度边界,遏制相应技术的发展。刑法稳定性与适应性及其辩证统一也是其在数字社会中保持正当性的两极支点。
这种适应性更新体现出一种“温和而坚实”的制度理性,即刑法应当以包容的方式面对新兴技术带来的行为形态变迁,在动态环境中保持规范的内在秩序。随着网络犯罪、数据侵权、信息操控等行为不断演化,刑法的回应机制应兼顾保守与适应性俱进,以此形成更具弹性的法益解释体系。通过制度层面的渐进调整与司法实践的案例化回应,刑法得以实现规范延展与社会适配的双重目标,使其在稳定与变革之间保持均衡。
同时,刑法的现代化并不仅限于立法层面,更体现在理念上的自我革新。数字安全治理须以法治原则为前提,以程序理性为保障。技术的进步不能凌驾于正当性原则之上,刑法的威慑力与权威性来自法治自身的理性约束。通过强化比例原则、明晰边界规范与完善程序保障机制,刑法不仅巩固数字安全体系的底线结构,也在科技变迁中守护法治文明的精神延续,这种适度、稳健、理性的制度姿态正是数字时代刑法应有的底色。
二、创新治理格局:刑法的边界与协调
数字中国战略的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而创新的驱动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结构,同时打破传统法律体系的稳定边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天然具有探索性与试验性,这意味着它既创造新机遇,也可能突破既有制度的风险防线。刑法的任务绝非压制这种活力,而是在创新与秩序之间建立制度平衡,使科技发展在开放中有边界,在自由中有规则。
刑法的边界功能首先体现为对创新风险的底线防御。数字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系统的高度协作之上,一旦信息失序或技术滥用,其影响往往呈现出连锁性和扩散性。刑法通过界定数字安全的核心法益确立风险行为的禁止性范围,从而使科技活动具备可预测的安全框架。不过,刑法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强化控制,更多在于维持制度平衡。科技创新的进步依赖制度的支持而非惩罚的威慑,刑法的协调功能体现在其对创新边界的精确刻画与对法律介入时机的审慎把握上。面对技术试验中的“灰色地带”,刑法不宜以僵硬的静态规则应对复杂的动态行为,而是应当通过建立风险分级制度与容错机制,为创新行为提供制度缓冲。区分故意滥用与技术误差、恶意侵害与非预见后果,能够有效防止刑事政策“泛化”,避免创新活力因惧刑而受抑。刑法的理性之处正在于它懂得“有所不为”,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保持法治的呼吸感。
从更深层次来看,刑法在创新治理中的意义不仅限于风险防控,更在于价值协调。科技创新不仅改变经济结构,也重塑社会价值系统。数据权、隐私权、算法公正与信息公平等新型法益的确立,使刑法承担起数字伦理的制度化使命。刑法通过明晰不可侵犯的核心利益,保障技术发展不背离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它所维护的不仅是“安全”本身,更是一种在技术扩张中保持人文底线的文明秩序。也正因如此,刑法在数字时代的价值不是遏制创新的工具,而是引导创新回归法治轨道的理性力量。
三、智能化治理:刑法现代化的理性自觉
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使得治理体系加速迈向智能化与数据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术的嵌入,不仅改变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也使法的实施逻辑出现结构性调整。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在顺应技术发展的同时,保持法治理性的内在稳定,使制度更新与正当性建设同步推进。
从侦查阶段来看,智能技术极大提升案件处理效率。算法识别、数据研判与数字追踪手段,使刑事侦查更具精准性与即时性。然而,这种效率的提升也带来潜在的权力风险。刑法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任何技术手段的使用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合法性标准。侦查机关在运用智能工具时,应建立权力行使的透明化与可审查机制,防止技术成为规避程序的“隐性权力”。刑法的合法性根基在于权力被约束的状态,只有在制度监督下的技术应用,才具备真正的法治正当性。
在司法环节上,算法辅助审判、量刑预测与数字证据系统的实验性应用极大提高工作环节的效率,但也带来“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的风险。算法的逻辑建立在统计归纳之上,缺乏人类法官的情境判断与价值衡量。刑法的核心是个案理性与道德判断,智能化不能削弱人的主体作用。司法实践应确立“算法可解释原则”与“人类审查优先机制”,保证技术手段服务于司法,而非反向支配司法。刑法的理性自觉,正体现在对技术权力的不断校正与自我约束之中。
进而言之,刑法的智能化转型是治理理念自我进化的结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申“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刑法的制度革新正是这一要求在法治层面的体现。智能技术的运用应当成为刑法体系优化的助力,而非价值取代的手段。可以通过建立数据治理标准、技术伦理指引与责任认定机制,使刑法在智能治理框架中保持自身的制度自治。刑法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以科技为工具、以法治为准绳,将价值判断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使数字时代的治理体系在效率与正义的张力中保持平衡。
综上所述,数字中国的建设,是科技革命与法治变革的双向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方针,为法治体系的现代化指明清晰的方向。刑法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红线与终极规范,在数字化演进中理应保持稳定而灵动的制度姿态——既不滞后于时代变革,也不超越其规范边界。刑法的现代化不仅是法律技术的演进,更是国家治理文明的自觉升华,在数字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刑法以底线之稳、理性之恒,构筑起科技发展与法治共荣的制度脊梁。
【作者曹波系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作者张钧宜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兜底罪名视阈中‘帮信罪’法理诠释与司法适用研究”(GDYB2023015)】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并将“统筹发展与安全”作为未来发展的总体要求。这一部署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而国家安全理念的数字化与法治化也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科技的快速进步不仅重塑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同时也带来风险形态、法益边界与制度逻辑的深层转变。刑法作为国家法治体系的底线规范,理应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大格局下实现理性革新——既坚守安全与秩序的制度底线,又能够与数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相适应,以制度定力与法治理性维系创新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一、数字安全格局:刑法秩序的适应与更新
数字中国建设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的整体重塑,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物理防御拓展至对数据、网络、算法及人工智能运行体系的系统性维护。信息基础设施与数据资源的稳定安全,直接关乎社会运行的韧性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性。刑法在这一结构中仍承担着制度“最后防线”的角色,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确立规范底线与法益边界,维护数字秩序的稳定结构。与行政监管或行业标准相比,刑法的介入始终代表着法治体系的终极约束。
在数字安全格局的演进过程中刑法并非主动治理力量,而是随时代演进自我调适的制度规范。面对新兴风险的复杂生成机制,如跨境数据流动引发的主权问题、算法失衡带来的社会操控、信息泄露导致的信任危机,刑法的回应不应当盲目扩张,而需要理性地通过适度修正实现法治体系的内部协调。刑法的应变逻辑体现在其审慎的特性——它既不能固守旧有结构而脱节于现实,亦不应因短期风险而突破制度边界,遏制相应技术的发展。刑法稳定性与适应性及其辩证统一也是其在数字社会中保持正当性的两极支点。
这种适应性更新体现出一种“温和而坚实”的制度理性,即刑法应当以包容的方式面对新兴技术带来的行为形态变迁,在动态环境中保持规范的内在秩序。随着网络犯罪、数据侵权、信息操控等行为不断演化,刑法的回应机制应兼顾保守与适应性俱进,以此形成更具弹性的法益解释体系。通过制度层面的渐进调整与司法实践的案例化回应,刑法得以实现规范延展与社会适配的双重目标,使其在稳定与变革之间保持均衡。
同时,刑法的现代化并不仅限于立法层面,更体现在理念上的自我革新。数字安全治理须以法治原则为前提,以程序理性为保障。技术的进步不能凌驾于正当性原则之上,刑法的威慑力与权威性来自法治自身的理性约束。通过强化比例原则、明晰边界规范与完善程序保障机制,刑法不仅巩固数字安全体系的底线结构,也在科技变迁中守护法治文明的精神延续,这种适度、稳健、理性的制度姿态正是数字时代刑法应有的底色。
二、创新治理格局:刑法的边界与协调
数字中国战略的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而创新的驱动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结构,同时打破传统法律体系的稳定边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天然具有探索性与试验性,这意味着它既创造新机遇,也可能突破既有制度的风险防线。刑法的任务绝非压制这种活力,而是在创新与秩序之间建立制度平衡,使科技发展在开放中有边界,在自由中有规则。
刑法的边界功能首先体现为对创新风险的底线防御。数字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系统的高度协作之上,一旦信息失序或技术滥用,其影响往往呈现出连锁性和扩散性。刑法通过界定数字安全的核心法益确立风险行为的禁止性范围,从而使科技活动具备可预测的安全框架。不过,刑法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强化控制,更多在于维持制度平衡。科技创新的进步依赖制度的支持而非惩罚的威慑,刑法的协调功能体现在其对创新边界的精确刻画与对法律介入时机的审慎把握上。面对技术试验中的“灰色地带”,刑法不宜以僵硬的静态规则应对复杂的动态行为,而是应当通过建立风险分级制度与容错机制,为创新行为提供制度缓冲。区分故意滥用与技术误差、恶意侵害与非预见后果,能够有效防止刑事政策“泛化”,避免创新活力因惧刑而受抑。刑法的理性之处正在于它懂得“有所不为”,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保持法治的呼吸感。
从更深层次来看,刑法在创新治理中的意义不仅限于风险防控,更在于价值协调。科技创新不仅改变经济结构,也重塑社会价值系统。数据权、隐私权、算法公正与信息公平等新型法益的确立,使刑法承担起数字伦理的制度化使命。刑法通过明晰不可侵犯的核心利益,保障技术发展不背离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它所维护的不仅是“安全”本身,更是一种在技术扩张中保持人文底线的文明秩序。也正因如此,刑法在数字时代的价值不是遏制创新的工具,而是引导创新回归法治轨道的理性力量。
三、智能化治理:刑法现代化的理性自觉
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使得治理体系加速迈向智能化与数据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术的嵌入,不仅改变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也使法的实施逻辑出现结构性调整。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在顺应技术发展的同时,保持法治理性的内在稳定,使制度更新与正当性建设同步推进。
从侦查阶段来看,智能技术极大提升案件处理效率。算法识别、数据研判与数字追踪手段,使刑事侦查更具精准性与即时性。然而,这种效率的提升也带来潜在的权力风险。刑法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任何技术手段的使用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合法性标准。侦查机关在运用智能工具时,应建立权力行使的透明化与可审查机制,防止技术成为规避程序的“隐性权力”。刑法的合法性根基在于权力被约束的状态,只有在制度监督下的技术应用,才具备真正的法治正当性。
在司法环节上,算法辅助审判、量刑预测与数字证据系统的实验性应用极大提高工作环节的效率,但也带来“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的风险。算法的逻辑建立在统计归纳之上,缺乏人类法官的情境判断与价值衡量。刑法的核心是个案理性与道德判断,智能化不能削弱人的主体作用。司法实践应确立“算法可解释原则”与“人类审查优先机制”,保证技术手段服务于司法,而非反向支配司法。刑法的理性自觉,正体现在对技术权力的不断校正与自我约束之中。
进而言之,刑法的智能化转型是治理理念自我进化的结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申“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刑法的制度革新正是这一要求在法治层面的体现。智能技术的运用应当成为刑法体系优化的助力,而非价值取代的手段。可以通过建立数据治理标准、技术伦理指引与责任认定机制,使刑法在智能治理框架中保持自身的制度自治。刑法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以科技为工具、以法治为准绳,将价值判断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使数字时代的治理体系在效率与正义的张力中保持平衡。
综上所述,数字中国的建设,是科技革命与法治变革的双向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方针,为法治体系的现代化指明清晰的方向。刑法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红线与终极规范,在数字化演进中理应保持稳定而灵动的制度姿态——既不滞后于时代变革,也不超越其规范边界。刑法的现代化不仅是法律技术的演进,更是国家治理文明的自觉升华,在数字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刑法以底线之稳、理性之恒,构筑起科技发展与法治共荣的制度脊梁。
【作者曹波系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作者张钧宜系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兜底罪名视阈中‘帮信罪’法理诠释与司法适用研究”(GDYB202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