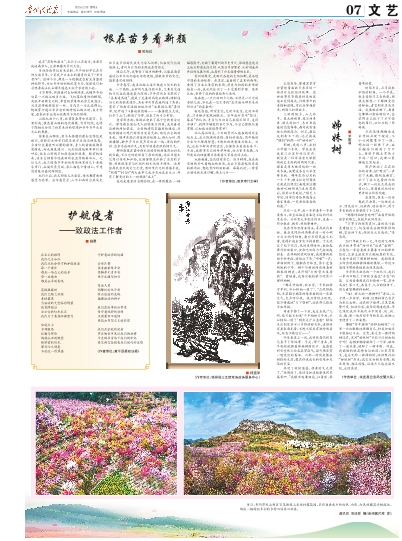发布日期:
根在苗乡看新颜
■ 欧知达
我是“苏黔结晶体”,生长于江苏南京,母亲是地道南京人,父亲祖籍为贵州天柱。
当初给我登记出生证时,爷爷奶奶早已在贵阳生活多年,于是我户口本上的籍贯就成了“贵州贵阳”。这四个字,像是一个被搁置在时光角落的神秘符号,亦如爷爷奶奶的浓厚乡音,深深吸引和召唤着我去认知那片遥远又似乎亲近的土地。
十岁那年,怀揣着对未知的渴求,我随爷爷奶奶第一次踏上回乡之旅。飞机落地贵阳的瞬间,我就开始暗自比较,市区的景象和南京大致相当,只是显得略微陈旧一些。当汽车一头扎进群山,蜿蜒穿行通往爷爷老家的崎岖山路上时,我才惊觉,原来世界还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模样。
山路九曲十八弯,地势复杂得如同迷宫。车里的我,强忍着山路的起伏颠簸、弯弯绕绕,也终于深切体会到了祖辈生活的艰难和爷爷当年走出大山的勇毅。
苗寨在山腰处,用木头搭建的屋舍显得很是破旧,静静伫立的它们像是被岁月遗忘的孤岛。乡亲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苗话,身上的苗族服饰虽有特色,却也褪色陈旧。他们热情地跟爷爷打招呼后,就去山野间不知疲倦地忙碌着。眼前的这些,让来自钢筋水泥森林的我显得格格不入。之后几天,我又陪着爷爷奶奶到县城里的几个亲戚家串门,县城风景秀丽,亲人相见乡情动人,可建筑的陈旧感同样明显。
此行之后,我又回过几次老家,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与思考。总体感觉是,山水如画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令人沉醉,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贵州与江苏的差距还是有些大。
随后几年,我暂停了返乡的脚步,只能在南京通过与爷爷奶奶通电话连视频,捕捉家乡的变化,想象着它的模样。
今年春节,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一下高铁,全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交通的变化让我感受最为深刻:多年前就全省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建成了完善的高速公路网;除联通兴义的高铁在建外,其余市州所在地均通了高铁;奠定了西南交通枢纽地位的“大数据之都”贵阳市,还开通了4条地铁线路……一条条康庄大道,打开了山门,联通了外界,送来了活力与希望。
老家黔东南,旅游业迎来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曾经藏在深山无人识的苗乡侗寨,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红景点。古老的建筑在翻新改造后,传统的韵味与现代的活力完美交融,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漫步在西江苗寨的石板路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脚步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周边的民宿、农家乐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
那些散落在苗岭侗水边的传统村落宛如时光的宝藏,不仅完好地保留了原始风貌,还让非遗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自然的宁静、传统的厚重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运用浓厚民族民间文化元素,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村超”“村BA”两大盛事已成为当地走出大山、外界了解贵州的又一对耀眼“名片”。
我还走进贵州省博物馆,在一件件展品、一幅幅影像中,全面了解贵州的历史变迁,深刻感受这片土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变得繁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历程,也看到了它充满希望的未来。
贵州的蝶变,是时代奋进的生动注脚,是奋进中国的生动缩影。在这里,我看到了真实的西部,看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将其与祖国的东部拼接在一起,我也就认识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这些认知,重塑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在想,一次次的回乡之路,不就是一次次的寻根之旅,不也在一次次寻找“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答案吗?
我还在想,所谓变化,无时不发生、无处不存在,只是缺少发现的眼光。当年我对贵州“陈旧、落后”的认识,是否与当初自己来得不够多、走得不够广、到得不够近的目之不及,与自己获取信息有限、认知能力较低等有关?
让人高兴的是,今日的贵州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用辛勤的汗水与无限的智慧,不断地改进着这片热土。而我,也会不断离开舒适区,去探索去创造去奋斗。今后,我将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助力家乡发展,力所能及地回报那片承载着父辈眷恋的土地。
血脉相连,总是情难自已。很多时候,我在南京的街头吃着鸭血粉丝汤,总会不禁想起黔东南的鹅肉粉、想起贵阳的肠旺面。每每此时,一种复合滋味就充盈口腔、涌上心头……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我是“苏黔结晶体”,生长于江苏南京,母亲是地道南京人,父亲祖籍为贵州天柱。
当初给我登记出生证时,爷爷奶奶早已在贵阳生活多年,于是我户口本上的籍贯就成了“贵州贵阳”。这四个字,像是一个被搁置在时光角落的神秘符号,亦如爷爷奶奶的浓厚乡音,深深吸引和召唤着我去认知那片遥远又似乎亲近的土地。
十岁那年,怀揣着对未知的渴求,我随爷爷奶奶第一次踏上回乡之旅。飞机落地贵阳的瞬间,我就开始暗自比较,市区的景象和南京大致相当,只是显得略微陈旧一些。当汽车一头扎进群山,蜿蜒穿行通往爷爷老家的崎岖山路上时,我才惊觉,原来世界还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模样。
山路九曲十八弯,地势复杂得如同迷宫。车里的我,强忍着山路的起伏颠簸、弯弯绕绕,也终于深切体会到了祖辈生活的艰难和爷爷当年走出大山的勇毅。
苗寨在山腰处,用木头搭建的屋舍显得很是破旧,静静伫立的它们像是被岁月遗忘的孤岛。乡亲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苗话,身上的苗族服饰虽有特色,却也褪色陈旧。他们热情地跟爷爷打招呼后,就去山野间不知疲倦地忙碌着。眼前的这些,让来自钢筋水泥森林的我显得格格不入。之后几天,我又陪着爷爷奶奶到县城里的几个亲戚家串门,县城风景秀丽,亲人相见乡情动人,可建筑的陈旧感同样明显。
此行之后,我又回过几次老家,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与思考。总体感觉是,山水如画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令人沉醉,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贵州与江苏的差距还是有些大。
随后几年,我暂停了返乡的脚步,只能在南京通过与爷爷奶奶通电话连视频,捕捉家乡的变化,想象着它的模样。
今年春节,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一下高铁,全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尤其是交通的变化让我感受最为深刻:多年前就全省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建成了完善的高速公路网;除联通兴义的高铁在建外,其余市州所在地均通了高铁;奠定了西南交通枢纽地位的“大数据之都”贵阳市,还开通了4条地铁线路……一条条康庄大道,打开了山门,联通了外界,送来了活力与希望。
老家黔东南,旅游业迎来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曾经藏在深山无人识的苗乡侗寨,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红景点。古老的建筑在翻新改造后,传统的韵味与现代的活力完美交融,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漫步在西江苗寨的石板路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脚步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周边的民宿、农家乐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
那些散落在苗岭侗水边的传统村落宛如时光的宝藏,不仅完好地保留了原始风貌,还让非遗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自然的宁静、传统的厚重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运用浓厚民族民间文化元素,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村超”“村BA”两大盛事已成为当地走出大山、外界了解贵州的又一对耀眼“名片”。
我还走进贵州省博物馆,在一件件展品、一幅幅影像中,全面了解贵州的历史变迁,深刻感受这片土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变得繁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历程,也看到了它充满希望的未来。
贵州的蝶变,是时代奋进的生动注脚,是奋进中国的生动缩影。在这里,我看到了真实的西部,看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将其与祖国的东部拼接在一起,我也就认识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这些认知,重塑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我在想,一次次的回乡之路,不就是一次次的寻根之旅,不也在一次次寻找“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答案吗?
我还在想,所谓变化,无时不发生、无处不存在,只是缺少发现的眼光。当年我对贵州“陈旧、落后”的认识,是否与当初自己来得不够多、走得不够广、到得不够近的目之不及,与自己获取信息有限、认知能力较低等有关?
让人高兴的是,今日的贵州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用辛勤的汗水与无限的智慧,不断地改进着这片热土。而我,也会不断离开舒适区,去探索去创造去奋斗。今后,我将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助力家乡发展,力所能及地回报那片承载着父辈眷恋的土地。
血脉相连,总是情难自已。很多时候,我在南京的街头吃着鸭血粉丝汤,总会不禁想起黔东南的鹅肉粉、想起贵阳的肠旺面。每每此时,一种复合滋味就充盈口腔、涌上心头……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